

發(fā)布時(shí)間:所屬分類:教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中國(窮得)三個(gè)人穿一條褲子,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中國種的是蘑菇云,收獲的是鵝卵石。但就在蘇聯(lián)毀約停援 5 年后,1964 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在大漠深處爆炸。赫魯曉夫獲知這一結(jié)果,或許會(huì)為當(dāng)初的斷言懊惱不已。 兩年零八個(gè)月后,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
“中國(窮得)三個(gè)人穿一條褲子,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中國種的是蘑菇云,收獲的是鵝卵石。”但就在蘇聯(lián)毀約停援 5 年后,1964 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在大漠深處爆炸。赫魯曉夫獲知這一結(jié)果,或許會(huì)為當(dāng)初的斷言懊惱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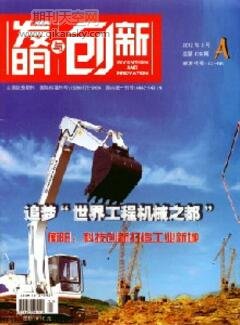
兩年零八個(gè)月后,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消息像爆炸產(chǎn)生的沖擊波,震撼了世界。沒有任何資料,沒有來自其他國家的任何幫助,完成“兩彈一星”(核彈、導(dǎo)彈、人造衛(wèi)星)實(shí)驗(yàn),對(duì)西方國家來說,驚人的速度是一個(gè)科學(xué)奇跡,更是一個(gè)不解之謎。
7 月 13 日,習(xí)近平同志在中央財(cái)經(jīng)委員會(huì)第二次會(huì)議上指出,突破關(guān)鍵核心技術(shù),關(guān)鍵在于有效發(fā)揮人的積極性,要將“兩彈一星” 精神發(fā)揚(yáng)光大,形成良好的精神面貌。
“兩彈一星”精神包括自力更生、大力協(xié)同、勇于攀登。“‘兩彈一星’是幾代人為之獻(xiàn)身的偉大事業(yè),更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財(cái)富,共同鑄就了中華民族的脊梁。”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杜祥琬院士表示,在 20 世紀(jì)五六十年代那個(gè)特定背景下干成這項(xiàng)事業(yè),首先離不開自力更生的科學(xué)精神。
奏響“自力更生”交響樂
“兩彈一星”這曲改變新中國命運(yùn)的交響樂,是數(shù)十萬人用生命合奏出來的。
在這首交響樂上,北京第六研究所(現(xiàn)中核集團(tuán)核工業(yè)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彈奏的是 “序曲”——生產(chǎn)制造原子彈的最初原料二氧化鈾。
1960 年 7 月,當(dāng)莊興海等滿懷豪情來到北京第六研究所時(shí),蘇聯(lián)專家已于 6 月突然提出終止合作,帶著資料回國。
莊興海回憶,二號(hào)廠籌建時(shí),除不銹鋼為進(jìn)口,包括陶瓷缸、陶瓷泵、搪瓷攪拌槽、動(dòng)力裝置在內(nèi)的材料設(shè)備全部實(shí)現(xiàn)國產(chǎn),并因陋就簡(jiǎn)采用了一些閑置設(shè)備:買不到不銹鋼閥門,就用試制的不銹鋼拷克替代;一時(shí)設(shè)計(jì)不出正規(guī)的熱分解爐,便設(shè)計(jì)制造簡(jiǎn)易的二氧化鈾煅燒爐,并用耐火瓷管代替供應(yīng)有缺口的耐火磚。
正是靠大家一股自力更生的干勁,經(jīng)過無數(shù)個(gè)日日夜夜的拼博,二氧化鈾簡(jiǎn)法生產(chǎn)廠建成了。
到 1962 年底,這個(gè)名字里既沒有“礦”也不帶“廠”的單位,提供了噸量級(jí)的高純度二氧化鈾和四氟化鈾,加速了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進(jìn)程。
“突破原理、物理設(shè)計(jì)、核地質(zhì)、核材料、冷試驗(yàn)(17 號(hào)工地)、熱試驗(yàn)、武器化……”杜祥琬說,自力更生貫穿我國核彈研制始終。
一張書桌、一把計(jì)算尺和一塊黑板是主要“兵器”
杜祥琬小時(shí)候的夢(mèng)想是研究天文學(xué),結(jié)果一輩子投身核物理。
被國家選擇,也被歷史選擇,人生軌道因此被改變的不止是杜祥琬。
1960 年 6 月,陳能寬先生突然接到通知:調(diào)入二機(jī)部核武器研究所,在他并不熟悉的爆轟物理領(lǐng)域,近乎白手起家,參加我國核武器研究,從此隱姓埋名 25 年。
1961 年 1 月,錢三強(qiáng)先生把于敏先生叫到辦公室,非常嚴(yán)肅、秘密地告訴他,希望他參加氫彈理論的預(yù)先研究。這次談話,改變了于敏的人生道路。一個(gè)月以后,35 歲的他被正式任命為“輕核理論組”的副組長。
北京應(yīng)用物理與計(jì)算數(shù)學(xué)研究所原所長李德元回憶,即使是我國核武器理論研究舉足輕重的人物,彭桓武先生當(dāng)時(shí)也并不知道氫彈是什么樣子。為搞清氫彈“模樣”,大家做過現(xiàn)在看來很“蠢”的事——把好幾個(gè)月的《紐約時(shí)報(bào)》借來,一頁一頁翻,希望找到蛛絲馬跡,可惜什么也沒有找到。
年輕探索者出發(fā)的陣地只有最基本的物理學(xué)原理,主要“兵器”是一張書桌、一把計(jì)算尺、一塊黑板、一顆火熱的心、一個(gè)不知疲倦的大腦。
北京花園路三號(hào)院 14 號(hào)樓,我國頂尖科學(xué)家曾在此為研制氫彈拼搏了兩年多。
當(dāng)時(shí)規(guī)定,每天晚上下班前要把所有材料統(tǒng)一存放在保密室,按張領(lǐng)取的草稿紙用完也要統(tǒng)一回收再由專人燒毀。一切工作只能在辦公室完成。所有人都主動(dòng)加班加點(diǎn),以至當(dāng)時(shí)室主任和支部書記的一項(xiàng)重要任務(wù)是晚上 10 點(diǎn)規(guī)勸人下班。許多人抹不開情面假裝離開了,瞅個(gè)空子又回到辦公室繼續(xù)挑燈夜戰(zhàn)。
在日復(fù)一日的計(jì)算中,科學(xué)奇跡誕生了。
精神的“基因”不隨時(shí)代改變
1999 年,《紐約時(shí)報(bào)》以 3 個(gè)版面刊出特稿:中國是憑本事還是間諜來突破核武發(fā)展?
在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shí),于敏指著報(bào)道說:“這句話說對(duì)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國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開始定的方針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無論是在研制原子彈、氫彈的年代還是現(xiàn)在,‘兩彈一星’精神是我們走有中國特色的科研道路,發(fā)展高科技的精神支柱。”82 歲的核武器工程專家胡思得院士說,當(dāng)年可能需要住帳篷、住“干打壘”,現(xiàn)在科研工作環(huán)境、條件改善了很多,但仍然會(huì)面對(duì)一些全新挑戰(zhàn)。
20 世紀(jì) 80 年代,在研究世界新軍事變革和大國軍事倡議調(diào)整時(shí),有人敏銳地注意到,世界大國特別是美國的軍事倡議調(diào)整,從“三位一體”的核霸權(quán)倡議,調(diào)整為“核與非核”的新霸權(quán)倡議,強(qiáng)化了國家導(dǎo)彈防御體系和基礎(chǔ)設(shè)施等非核手段。
杜祥琬說,像發(fā)展核武器一樣,我國發(fā)展非核新概念武器同樣是從本國倡議需求出發(fā),這些差別又會(huì)延伸到應(yīng)用結(jié)構(gòu)的格局,例如形成本國特色的“空天一體”的體系概念。
“精神文化是一種非常硬的軟實(shí)力,是物質(zhì)不可替代的力量。”在杜祥琬看來,在價(jià)值觀多元化的今天,傳承和弘揚(yáng)“兩彈一星”精神,武裝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是意義深遠(yuǎn)的一項(xiàng)基本建設(shè)。
期刊推薦:《發(fā)明與創(chuàng)新(大科技)》本刊是中國發(fā)明協(xié)會(huì)主辦的專事報(bào)道發(fā)明創(chuàng)新的綜合性月刊。它以弘揚(yáng)創(chuàng)新精神、普及發(fā)明創(chuàng)新知識(shí)、探討創(chuàng)造力開發(fā)、傳播新發(fā)明新產(chǎn)品信息為宗旨,竭誠為各行各業(yè)的發(fā)明創(chuàng)新者及愛好者服務(wù),為發(fā)明創(chuàng)新成果的轉(zhuǎn)化牽線搭橋。《發(fā)明與革新》設(shè)有:創(chuàng)新論壇,發(fā)明參謀,創(chuàng)造探幽,精英譜,創(chuàng)意與設(shè)計(j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市場(chǎng)與營銷,創(chuàng)造教育,未來發(fā)明家,環(huán)境傳真,文明的腳步,世界真奇妙,創(chuàng)造博覽,爭(zhēng)鳴與探討,科幻文藝,我與發(fā)明,靈機(jī)一動(dòng),點(diǎn)子與竅門,動(dòng)態(tài)一覽,新發(fā)明新產(chǎn)品,發(fā)明市場(chǎng)等欄目,內(nèi)容新穎,文圖并茂,是各行各業(yè)的發(fā)明創(chuàng)新者和廣大青少年開發(fā)創(chuàng)造力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