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時間:所屬分類:工程師職稱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為探究循環沖擊損傷后大理巖的靜態斷裂力學特征,基于有限差分(FDM)-離散元(DEM)耦合的建模技術構建了三維分離式霍普金森壓桿(SHPB)數值模型,其中桿件系統和巖石試件分別采用FLAC3D和PFC3D程序建模。利用該模型對中心直切槽半圓盤(NSCB)試樣進行了恒
摘要:為探究循環沖擊損傷后大理巖的靜態斷裂力學特征,基于有限差分(FDM)-離散元(DEM)耦合的建模技術構建了三維分離式霍普金森壓桿(SHPB)數值模型,其中桿件系統和巖石試件分別采用FLAC3D和PFC3D程序建模。利用該模型對中心直切槽半圓盤(NSCB)試樣進行了恒定子彈速度下的循環沖擊,隨后對受損試樣進行靜態三點彎曲斷裂試驗。通過編寫Fish程序,提取試樣斷裂面數據,對斷裂面進行重構并定量計算表面粗糙度。通過與相關室內試驗結果的對比分析,驗證了本文數值分析的合理性與可靠性。模擬結果表明,隨著循環沖擊次數的增加,試樣內部微裂紋、破碎顆粒均增加。連接力場分布混亂,部分力鏈發生斷裂。力鏈的變化是試樣力學性能劣化的根本原因。在靜態三點彎曲斷裂試驗中,沖擊5次后的試樣的靜態斷裂韌度較天然試樣降低53.35%。試樣在靜載過程中會產生微裂紋和碎塊的數量隨著循環沖擊次數的增加而增加。斷裂面粗糙度隨循環沖擊次數的增加而增加。研究結論可為工程實踐提供一定指導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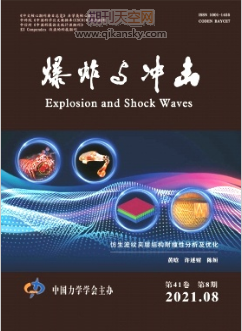
關鍵詞:巖石力學;有限差分-離散元耦合;霍普金森;循環沖擊;斷裂韌度
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地下資源和空間的開發利用規模日益增大[1,2],勢必帶來大量的地下巖體開挖掘進工作,而鉆爆法在我國仍是目前最常用的施工方法[3]。炸藥爆炸破碎巖體的同時,也會導致地下工程預保留圍巖的動態擾動、損傷甚至破裂[4,5]。循環爆破后,圍巖將受到不同程度的累積動態損傷[6,7],導致其在承受地應力重分布帶來的靜態荷載時斷裂韌度下降、承載能力大幅劣化,極易引發各種工程事故。因此,循環沖擊損傷后巖石的靜態斷裂特征研究具有較強的工程意義。
學者們對脆性巖石在循環沖擊作用下的疲勞特性進行了大量研究[8-10],但現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循環沖擊下巖石損傷、破裂直至完全破壞全過程。如Li等[11]采用霍普金森壓力桿系統(splitHopkinsonpressurebar,SHPB)對花崗巖進行了循環沖擊加載試驗,結果表明,當沖擊氣壓在一定范圍內時,每次沖擊都會對巖石造成動態損傷但不至于完全破壞;林大能等[12]研究了循環沖擊作用下圍壓、沖擊氣壓和沖擊次數對巖石動態損傷的影響;王彤等[13]利用動靜組合加載裝置進行不同軸壓、不同沖擊氣壓下的循環沖擊試驗。而在受損巖石的靜態斷裂特性研究方面,損傷誘因也多以環境因素為主,如左建平等[14]探究了不同溫度影響后花崗巖的細觀斷裂機制;賀晶晶等[15]分析凍融損傷對砂巖斷裂性能的劣化影響,并對試樣斷裂破壞面的形貌特征進行了掃描分析;楊建峰等[16]研究了不同程度水損傷作用對泥巖斷裂力學特性的影響。
低能量密度的循環沖擊能導致巖石的累積動態損傷乃至破裂,但是并不能致使其完全破壞,此時巖石仍有一定的承載能力[17]。但是,目前涉及循環沖擊損傷后巖石靜態承載能力的研究鮮有報道。雖然付安琪等[18]利用SHPB系統對中心直切槽半圓盤(notchedsemi-circularbend,NSCB)大理巖試樣進行了循環沖擊損傷處理,然后對其進行靜態斷裂試驗,分析了動態損傷對大理巖斷裂力學性能的劣化影響。但是巖石材料離散性較大,試驗結論適用范圍有限。此外,由于室內試驗研究條件的局限,該論文未能對動態損傷累積過程及靜態斷裂力學行為劣化機制進行深入研究。
隨著現代計算技術的不斷發展,多種數值分析方法被用來構建SHPB模型并進行動態沖擊試驗,如有限元軟件ABAQUS[19]、AUTODYN[20],及離散元軟件PFC[21,22]等。由于桿件由高強度鋼材加工而成,而巖石試樣是強度相對較低的脆性介質,在沖擊試驗過程中,桿件僅發生形變,而巖樣則將發生破裂甚至破碎。因此,桿件系統利用連續介質模型模擬,同時巖石試樣利用離散介質模擬是較為理想的數值建模方法。此外,僅采用三維離散元方法模擬SHPB試驗時,只能通過提高桿件顆粒接觸粘結強度來近似滿足“應力均勻性假定”[23],并且桿件模型顆粒間的孔隙率對模擬結果準確性也有一定影響。而連續-非連續耦合的建模方法則可以上述缺陷進行有效的改善,并能顯著提高計算效率,但目前這種耦合技術很少被應用于SHPB試驗的模擬。
鑒于此,本文利用Itasca公司開發的FLAC3D(基于有限差分方法FDM)和PFC3D(基于離散元方法DEM)系列程序構建了三維SHPB耦合模型。利用該模型對模擬NSCB試樣沿厚度方向進行不同次數的循環沖擊預損傷試驗,隨后對受損試樣進行靜態斷裂韌度模擬試驗,驗證了相關室內試驗研究的結論,并結合微裂紋場、力鏈場等機理信息對動態損傷累積過程及斷裂力學性能劣化機制進行深入研究。
1模型描述
1.1循環沖擊試驗
三維FDM-DEM耦合SHPB模擬系統如圖1所示。其中桿件利用FLAC3D中的線彈性模型建立,尺寸及材料參數與室內試驗一致[18];NSCB巖樣是基于PFC3D構建的離散顆粒粘結體,并選擇了能夠重現加載過程中的微裂縫萌生、聚結和宏觀裂縫形成的平行黏結模型(parallelbondingmodel,PBM),其尺寸構型與室內試驗一致[18]。與大理巖三點彎曲室內試驗結果反復對比反饋,通過“試錯法”對模擬試樣細觀參數進行標定,最終獲得一組能夠反映脆性大理巖力學特性的細觀參數,見表1。
應力波對比如圖2所示,可以看出模擬波形與實驗波形有很好的一致性。入射波和反射波之和近似等于透射波,并且在峰值后一定時間內仍保持相等。由此可見,本次模擬可實現試樣的動態受力平衡。與室內試驗一致[18],所有試樣分為6組,利用SHPB系統對各組試樣沿厚度方向分別進行了0~5次沖擊速度v均為4m/s的等能量沖擊,以獲得損傷程度不同的6組巖樣。
1.2靜態三點彎曲斷裂試驗
預損傷試驗完成后,將子彈與桿件移除。在受損試樣的底部加設兩根支撐鋼棒,并在試樣上側以0.06mm/min的恒定速率施加荷載[18],如圖3所示。圖4給出了完整試樣靜態三點彎曲試驗中荷載-位移曲線的室內試驗[18]和數值模擬結果對比。可見模擬獲得的試樣峰值荷載及破壞位移均與試驗結果一致,即表1所示細觀參數較為合理。
2循環沖擊結果分析
2.1應力波信號
圖5給出了首次沖擊時桿件中的應力波傳播過程。t=0μs時,子彈撞擊桿件,產生的壓縮波由入射桿左端進入SHPB系統。t=409μs時,壓縮波到達試樣的左端,隨即產生拉伸波(即反射波)向入射桿左端方向傳播。剩余應力波到達試樣右端時,再次發生反射-透射,透射波作為壓縮波向右端傳播。需要注意的是,在反射拉伸波之后,有一個壓縮波沿著入射桿向左端傳播(圖5黑色線框內)。這是因為在相對較小的沖擊速度下(4m/s),試件在加載期間(入射波上升段)未被完全破壞。在卸載期間(入射波下降段),試樣中儲存的部分應變能將沿著入射桿釋放,即發生回彈現象,從而產生壓縮波,這與Li[23]的結論一致。
圖6為循環沖擊過程中的應力波信號疊加圖。從圖中可以看出,入射波幅值在每個沖擊周期中基本重合,說明模擬實現了等幅循環加載。隨著循環次數的增加,透射波的幅值越來越小,而反射波則越來越大。主要原因為在循環沖擊作用下,巖石內部損傷累積,巖石孔隙率增加,而波阻抗降低[24]。與應力傳播過程圖一致,在卸載段,入射桿上采集到的應力波信號有一段為負值,對應上述回彈現象。
2.2動態應力-應變曲線
圖7為模擬試樣在循環沖擊過程中的動態應力-應變曲線,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彈性變形階段、裂紋擴展階段和應力卸載階段[24]。在彈性變形階段,軸向應變幾乎隨動態應力的增加而線性增加。隨著應力的進一步增大,試樣進入微裂紋擴展階段,微裂紋萌生、擴展并相互作用,導致曲線呈現非線性行為。應力卸載過程對應于曲線的峰后段。
圖8為峰值應力試驗值與模擬值變化對比。當沖擊次數由1增長至5時,峰值應力模擬值從105.45MPa降低到75.76MPa,降幅為28.16%,試驗值由103.94MPa降低到72.30MPa,降幅為30.44%。另一方面,隨著沖擊次數n的增大,峰值應變增大。隨著沖擊次數的增加,原生裂紋擴展,同時大量的新裂紋萌生,卸載階段試樣恢復的應變能降低。
2.3動態損傷演變
PFC3D程序中,試樣顆粒之間的粘結斷裂即視為產生了微裂紋,微裂紋擴展嚴重區域常伴隨著顆粒脫落,形成碎塊。圖9給出了循環沖擊過程中模擬試樣裂紋場及碎塊場的演變過程。從圖9中可以直觀了解到循環沖擊過程中試樣內部動態損傷演變過程:隨著沖擊次數的增多,試樣內部微裂紋及碎塊數目均有明顯上升。圖9b紅色框內為撞擊掉落顆粒,與室內試驗結果(圖9c)中觀察到的白斑及邊緣掉落顆粒一致,為巖石顆粒在動載作用下相互錯動導致[25]。
為定量分析,圖10給出了微裂紋數量Nc及碎塊數量Nf隨加載次數n的變化規律。可見試樣損傷演變過程可以劃分為急劇增長階段,緩慢發展階段和急劇增長階段:當n=1時,首次沖擊造成的損傷較大,Nc及Nf分別由0增長至3558和32;當n=2-4時,單次造成的損傷較小,沖擊4次后的Nc及Nf分別為6402和58;當n=5時,單次造成的損傷較大,Nc及Nf分別增長至11331和198。
模擬試樣顆粒之間具有粘結力,形成的力鏈在受到荷載作用時會改變,甚至斷裂。因此,力鏈演變能夠揭示受損試樣的動態損傷累積機理[26]。圖11給出了每次沖擊后試樣接觸力場(剖面圖)演變過程。
由圖可見,在動態荷載沖擊作用下,試樣內部力鏈分布均勻性變差,部分力鏈發生斷裂。當n=5時,試樣力鏈出現區域性缺失(黑色虛線框內)。此外,試樣部分區域出現明顯的應力集中(紅色虛線框內),且均與室內試驗中試樣白斑及顆粒掉落位置一致。力鏈的斷裂及缺失使試樣在受到后續荷載作用時更易被破壞,這是受損試樣力學特征劣化的根本原因。
為了驗證上述微觀結構變化,圖12給出了受損試樣內部結構偏光顯微結果。穿晶裂紋和沿晶裂紋的數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試樣結構的損傷程度。可以看出,天然狀態下礦物顆粒完整,沒有明顯微裂紋。然而,經過動態沖擊后,顆粒之間粘結強度降低。n=1時,可以觀察到明顯裂紋,說明巖石內部結構已被破壞。當n=2、3時,裂紋數目增多,且周圍晶體顆粒的破碎程度明顯增加。當n=4、5時,裂紋已發生合并,發展為宏觀裂紋,周圍的晶體顆粒幾乎完全破碎,大理巖試樣內部結構的動態損傷已經非常嚴重。
3三點彎曲結果分析
3.1荷載–位移曲線
圖13給出了受損試樣靜態荷載 位移曲線的模擬結果及試驗結果。模擬曲線包含:(1)線彈性階段:荷載隨位移線性增長;(2)脆性破壞階段:試樣發生脆性斷裂,荷載瞬間跌落。隨著循環沖擊次數的增長,試樣內部損傷程度加劇,裂紋數目增長,曲線壓密段持續時間相應增長,而彈性段斜率隨著沖擊次數的增長而降低。模擬試樣曲線整體趨勢與室內試驗結果一致。
3.3試樣破壞特征
圖15給出了模擬試樣斷裂破壞后的裂紋場及碎塊場演變。可以看到,受損試樣的破壞形式均為典型三點彎曲斷裂破壞:從預制裂縫的頂端處起裂,擴展至加載點附近。
圖16給出了靜態加載過程中新增微裂紋及碎塊數量隨循環沖擊次數n的變化規律。隨沖擊次數的增加,受損試樣力鏈斷裂部分越來越多,導致靜態加載過程中更多的微裂紋萌生并擴展。n由0增長至5時,新增微裂紋及碎塊數量分別由1429、11增長至1887、34。當外部荷載作用于試樣,其內部所形成的集中應力大于試樣損傷閾值時,接觸斷裂,微裂紋產生。而當外部荷載、參與試樣變形的總接觸數量一定時,接觸斷裂現象越明顯,說明試樣將越易發生宏觀破裂。結合圖13(a)所示,較天然試樣,n=1~5時,試樣剛度下降幅度分別為27.23%,36.05%,39.38%,55.53%,76.59%。因此,試樣的抗變形能力隨著沖擊次數的增加而逐漸減小。
對破壞后的試樣斷裂面利用surfer軟件進行后處理,得到斷裂面重建圖,如圖17所示。為定量表征斷裂面粗糙度,本次研究采用斷裂面輪廓高度均值(Sa),斷裂面輪廓最大最小高度差值(Sz)對斷裂面進行精確化描述。
由圖18可知,斷裂面粗糙度隨沖擊次數的增加而增加。較天然狀態,循環沖擊5次受損試樣斷裂面的Sa,Sz分別增長了32.06%,27.70%。在動態荷載作用下,微裂紋在試樣內部隨機產生,介質非均勻性、非連續性程度升高,致使試樣破裂面粗糙度上升,與室內試驗結論一致[18]。
4結論
本文基于有限差分法FDM及離散元方法DEM耦合思想,利用FLAC3D及PFC3D軟件構建了三維SHPB模型。利用該模型對NSCB試樣進行沿厚度方向的等能量循環沖擊,隨后對受損試樣進行靜態三點彎曲試驗,探究了大理巖試樣在循環沖擊作用下動態損傷累積機理及受損試樣的靜態斷裂力學特征劣化機制。主要結論如下:
(1)壓縮作用下的應力波信號與試驗結果較吻合,從而驗證了FEM-DEM耦合SHPB系統用于動力加載的可行性。此外,微裂紋場、碎塊場、接觸力鏈結構、峰值強度、斷裂韌度等特征均與試驗結果吻合。
(2)在較低動態荷載作用下,應力-應變曲線會因試樣在卸載段釋放應變能而產生回彈。隨著循環沖擊次數的增加,試樣雖未發生整體破碎,但內部微裂隙、破碎顆粒、斷裂力鏈數量均增加,其動態峰值應力降低,動態損傷不斷累積。
(3)受損試樣的靜態斷裂韌度較天然試樣明顯劣化,破壞應變則呈上升趨勢。隨著沖擊次數的增加,試樣力鏈斷裂現象愈發明顯。試樣介質非均勻性、非連續性程度在循環沖擊過程中不斷升高,致使試樣破裂面粗糙度上升斷裂面粗糙度增加。——論文作者:張濤1,蔚立元1,蘇海健1,羅寧1,魏江波2
相關期刊推薦:《爆炸與沖擊》雜志報道爆炸力學學科領域的國內外最新科技成果,反映學術前沿進展及水平,促進學術交流,創造本學科領域青年人才良好的成長環境,推進爆炸理論和應用、抗爆與爆炸安全技術的發展。主要讀者對象為從事爆炸物理、巖土爆炸、工程和器材爆炸等方面的科技人、員工程設計人員和高等院校師生。